内容提要:黑格尔批评卢梭用契约论来处理国家政治问题是把国家公权力错置于私人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众意”来充当“公意”或“普遍意志”,认为这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的理论上的原因。但黑格尔误解了卢梭的公意,卢梭的公意有其哲学基础,他对公意和众意做了区分,并清醒地认识到由公意所建立起来的完美的民主制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只是用来促使现实国家政治生活在众意的行使中日益趋向接近的标准,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法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黑格尔所理解,卢梭并不能为法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卢梭的公意除了有理性的根源外,还有公民宗教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公意只有凭借理性和信仰的双管齐下才能对公民社会的建立和运行产生有效的影响。厘清卢梭的这一套以公意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法治社会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Hegel criticizes that Rousseau mistakenly bases public (national) power on the relation to private property when he use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government and replaces “general will” or “universal will” with “will of all”.Hegel maintains that this is the very theoretical cause which leads to the traged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Unfortunately,Hegel misunderstands Rousseau’s concept of “general will”.The general will in Rousseau’s thought has its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Rousseau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will and the will of all and fully realizes that the perfect democratic institution founded by the general will is an ideal utopia which should be used only as a standard to guide the real political life driven by the will of all.Unfortunately,it is misunderstoo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and Hegel as well.Rousseau is not the person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Besides its root in reason,Rousseau’s “general will” also has its origin in civil religion and the ethos and customs along with it.In the real political life,it is by the co-effect of reason and belief that the general will could contribute validly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To clarify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with the general will as its core idea is significant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a society ruled by law today.
关键词:社会契约/公意/众意/法国革命/理性/宗教/social contract/general will/will of all/French Revolution/reason/religion
一、黑格尔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多处涉及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公意”学说。例如,在《契约》一章第75节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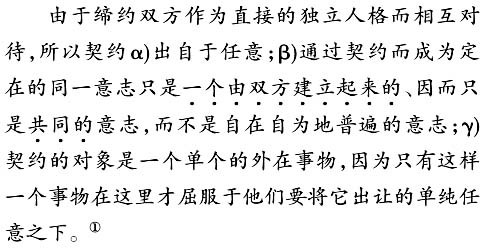
显然,以上契约的三环节是立足于私有财产关系之上的,即:一个是任意(Willkür);一个是“共同意志”(der gemeinsamer Wille),而不是“普遍意志”(der allgemeiner Wille);再一个是出让的财物。②黑格尔指出,在“伦理”(Sittlichkeit)的三大部分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中,契约只适合于市民社会,而不适用于家庭和国家原则。这里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契约论的国家学说的,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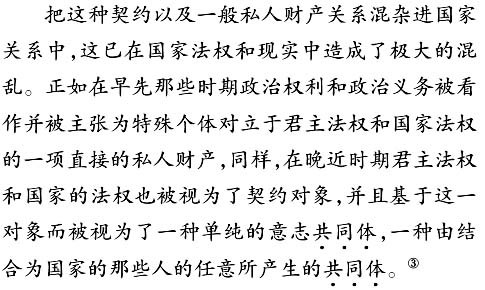
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早先那些时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前后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时期,这些社会契约理论承认君主和国家的法权,却使这种法权基于每个个体的同意之上,但又置于公民立法权的对立面,最终则形成了洛克(及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论。而所谓“晚近时期”则特指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时君主和政府本身也被视为公民立法的产物,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和全体订立的契约成了新型国家的基础。按照黑格尔的意思,这些社会契约在这种理解中都类似于一种财产关系的转让契约,是不恰当地“把私有财产的规定搬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且更高的领域”。④因此黑格尔补充道:
但在国家那里,情况却另是一样,因为不能由于个体的任意而脱离国家,一个人按照其自然方面来说就已经是国家的公民了。人的理性规定就是要在国家中生活,并且当国家还不存在时,理性对建立国家的要求就现成地存在了。……所以这决非依赖于个别人的任意,因而国家并非基于以任意为前提的契约之上。……毋宁说,处于国家之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是自在自为地保持这同一个目的,而不能每个人在与这一目的相关时都像在中世纪那样按照自己的私人约定来行事。⑤
换言之,在私有财产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共同意志”,即缔约各方的各自任意( )所达成的共同性;相反,在国家中所贯彻的则是“普遍意志”,它不是通过每个人投票所确定的,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本性,有理性的人生来就是要在国家中过政治生活的,没有人真正愿意和能够遗世独立。所以,普遍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是一种更高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一种人为建立的契约关系。它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高兆明先生指出,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他“以公民必须生活在国家中混淆、代替了公民对于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对于国家本身合理性根据的追问”⑥。而契约论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国家公权的合理性,必须从私权中寻求,必须从私权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⑦。这是很有见地的。黑格尔把契约仅仅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财物的交易,这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且不说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就不是什么财产关系,而是精神信仰的契约;而且即使是世俗的契约关系,也不全是针对“单个的外在事物”。例如,知识产权就不是对物的拥有和交换,而是对思想观念的拥有和交换,所以黑格尔无法从法律上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只好把它归结为一个“面子”问题,“并依靠面子来制止它”。⑧至于像美国立国时那样通过约定宪法来规定政体形式(更不用说美国宪法的前身、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了),黑格尔连提都不提。其实,只要不把“契约”的内涵规定得那么狭窄,则婚姻关系和国家法律以至于宗教信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
黑格尔在这里还没有直接点卢梭的名字,而在后面谈国家的部分,他就明确指出他所针对的主要就是卢梭的“公意”学说。他首先承认,卢梭在国家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其卓越的贡献,即在卢梭眼里,以往把国家的产生归结到人类的社会性本能或神的权威,这只是外部的形式,它的内容其实是“思想”或“思维本身”,也就是“意志”;但卢梭这里所理解的意志就其层次来说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成为国家原则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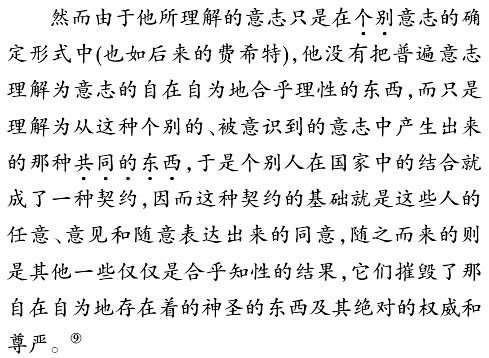
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就是一方面试图砸烂一切现行的制度而仅凭思想来从头建立一个国家,想要给这个国家一个建立在被以为是合乎理性的基础上的宪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这只是些缺乏理念的抽象,于是就把这场试验变成了极恐怖极残忍的一场事变。⑩这就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即归咎于卢梭的“公意”,这种公意由于只被理解为“共同的东西”,即共同意志,因而就下降为一种临时性的契约,从“合乎理性的东西”(Vern nftige)降低成了“仅仅是合乎知性的(verst ndig)结果”。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卢梭的错误就在于把“公意”仅仅理解为“共同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任意的契约,而不是神圣的伦理原则。(11)而正确的理解则应当把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理念之上,这样就可以看出: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理性的绝对目的就是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国家就是竖立在人世上的精神,它在人世上有意识地实现着自身……只有当它在意识中现成在手并把自己当作实存的对象来认知时,它才是国家。至于自由,我们必须不是从个别性、从个别自我意识来看它,而是只从自我意识的本质来看它,因为不论人是否知道,这个本质都在作为独立的力量而实现着自己:国家存在着,这就是神在人世上行进,国家的基础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身的理性的力量。谈到国家的理念,我们必须不是着眼于那些特殊的国家,着眼于那些特殊的制度,反之,我们必须自为地考察理念,考察这个现实的神。(12)
黑格尔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来对抗他所认为的卢梭(和费希特)把国家建立在个体意志之上的主观主义。他这种将国家神化的观点历来都饱受诟病,现代人不能容忍说一个国家即使已经恶劣不堪,也得像对神一样无条件地服从(13),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正是主张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政府,以治疗国家的疾病。黑格尔的观点则堵死了这条人民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善国家的道路,在他看来,改善国家不是人民的事,而是“神”的事,也就是绝对精神通过世界历史的淘汰即国家间的战争而客观上展示出国家精神日益进步的趋势。黑格尔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国家意志不应当仅仅是大多数人甚至哪怕所有的人的“共同意志”(因为这是随时可变的),而应当是更高层次上的“普遍意志”(这是永恒不变的,哪怕它还潜在于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中)。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用这一点来批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算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尽管有许多表述上的含混和不清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强调的恰好正是黑格尔所主张的“普遍意志”,所谓“公意”和“众意”的区别也是卢梭反复阐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卢梭正好是将公意置于哲学认识的层次而超拔于具体操作的众意层次之上,因而并不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法国大革命和它的领袖及理论家们忽视了这一区别,从而用众意取代了公意而已。下面我就来证明这一点。
二、黑格尔对卢梭的误解:什么是“公意”?
说到底,黑格尔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误解归结为对所谓“公意”的误解。那么,什么是卢梭的“公意”?它与“众意”的区别何在?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国家的产生如果真像霍布斯和格劳秀斯所说的必须基于一个社会契约的话,那就“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公约”。比如说,全体人民通过投票而选举出了一位国王,这种投票按照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然也包含零票服从全票这一罕见的情况);然而——
事实上,假如根本就没有事先的约定的话,除非选举真是全体一致的,不然,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抉择这一义务又从何而来呢?同意某一个主人的一百个人,又何以有权为根本就不同意这个主人的另外十个人进行投票呢?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14)
卢梭的这段话,很容易被人马虎对待,而以为少数服从多数就代表了“最初的约定”(公意)。(15)但这是不能等同的,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规则,即众意,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例如,在战争时期就需要多数服从少数,甚至全体服从一人(统帅),对专业技术问题则必须服从专家;又如,在对待人的生命问题上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像“文革”中有的地方根据95%的群众的意见就处死5%的“四类分子”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义的,属于“多数的暴政”)。而“最初约定”则必须基于所有人的普遍意志,它是制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或者其他原则的初始标准,凡未经这一标准批准的规则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卢梭强调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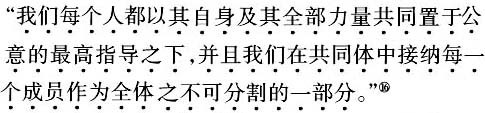
可见,把法国大革命的“多数暴政”和血腥动乱归咎于卢梭是多么的不公平。
从本质上看,卢梭的公意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约,虽然在选举问题上这种公意通常都会全体一致地同意采用多数原则,但它本身决不等同于少数服从多数,甚至也不等同于选举中100%的票数。为此,他把公意又称为“公共的大我”或“公共人格”,(17)即不是一次性的投票所体现的暂时的一致性,而是像人格一样具有时间中的前后一贯性和永恒不变性。(18)在这里,有必要把卢梭这几个概念的原文辨析一下。总的来说,卢梭把意志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个别意志(volonté particulière),第二种是团体的意志(volontè de corps),第三种是众意(volonté de tous),最后第四种才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19)而公意的“公”字即générale,其首要的义项为“概括的”、“一般的”、“普遍的”、“通常的”;其次是“笼统的”、“空泛的”;第三才是“总的”、“全体的”。(20)所以,“公意”的意思首先就是“普遍意志”,但有时候也免不了被理解为“全体意志”,它不像德语的“普遍意志”(del allgemeine Wille)那样并不包含“全体意志”的意思。当然,黑格尔是懂法文的,但不知他是否仔细研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恐怕更多地是从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论家那里获悉卢梭的契约论思想的。例如,他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谈到法国革命的原则时说:
这种意识所意识到的,是自己的纯粹人格性以及其中的一切精神实在性,而一切实在性都只是精神性的东西;对它而言这个世界完全是它的意志,而它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更确切地说,普遍的意志并不是那种建立在默许或被代表的赞同之中的、关于意志的空洞思想,而是实在的普遍意志,是一切个别人本身的意志。(21)
这段话应该就是黑格尔对法国革命中所打出的“公意”旗号的一种解释,即公意和众意的等同,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个旗号的无条件的赞同。德文考证版的编者在这里加了一个编者注:“此处黑格尔明显引用了法国大革命宪法学家西耶斯(Emmanuel Sieyès,1748-1836)的说法,参看德译本《西耶斯政治著作全集》第1卷,1796年,第207页:‘为了共同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意志是必须的。这个共同意志当然应该是一切个别人的意志的普遍的总和;而结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中的全体人们将会有的共同意志,毫无疑问恰好就是一切个别人的意志的总和。’”在这里,“一切个别人的意志的总和”就是西耶斯(又译西哀士)对卢梭的“公意”的理解,即理解为一切个别人的“共同意志”(der gemeinschaftliche Wille)(22),而这很可能正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卢梭的“公意”的来由和出处。换言之,他是借助于西耶斯的(自以为)对卢梭的解释来理解卢梭的。不过他也在这种理解中加进了他自己的观点,即普遍意志一旦付诸实施,就会成为“一切个别人本身的意志”,即成为“共同意志”,从而偏离了普遍意志的理念,甚至成了普遍意志的自否定。其结果必然是:教化世界中的所有那些规定“都通过自我在绝对自由中所经验到的损失而失去了;它的否定是毫无意义的死亡,是那本身不具有任何肯定性的东西、不具有任何充实内容的否定东西的纯粹恐怖。——但同时,这种否定在其现实性中并不是一种异己的东西 ;相反,它是普遍的意志 ,这普遍意志在自己这种最后的抽象中不具有任何肯定性东西,因而不能从牺牲中得到任何回报”(23)。就是说,普遍意志的绝对自由一旦在现实中实现为共同意志和国家原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法国革命那样的恐怖。这倒是对的。
但问题在于,卢梭是否主张普遍意志或公意能够直接作为现实中的国家法律来操作呢?我们只要仔细阅读一下《社会契约论》,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卢梭认为,国家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因为“众意”总是有可能出错的,人民“往往会受欺骗”,哪怕全体一致同意的事也可能是错的;但“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卢梭尽量想要通俗而简明地阐明公意和众意的区别,他因此采取了这样笨拙的表达方式:
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24)
之所以说是“笨拙的表达方式”,是因为这样分别出来的公意,仍然和众意处于同一个水平,并没有从本质上拉开档次;另外,若要严格推敲起来,个别意志的总和中除掉正负相抵的部分,剩下的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公意,因为其中有些可能是众意的重合,大家一起犯错误。但其中肯定包含有公意,则是显然的。类似的表达还有在谈主权不可分割时说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25)李平沤先生在解释这句话时这样说道:“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一切决定,要么是由全体人民作出的,也就是说出自公意,从而形成法律;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出自个别意志……只是一种行政行为,而不能形成法律。”(26)这种解释如果是正确的话,那卢梭就够愚蠢的了,他竟会认为只要有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即不是“由全体人民作出的”决定,就“不能形成法律”。但卢梭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并不等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卢梭似乎早料到会出现李先生的这种误解,他在这句话中间加了一个注:“意志要成为公意,并不永远需要它是全体一致的,但必须把全部票数都计算在内;任何形式的例外都会破坏它的公共性。”(27)李先生这种误解类似于黑格尔的误解,但情有可原的是,卢梭本人的表达不清楚也是要为此负责的。例如,他在《爱弥儿》所载的《游历》一文中,为了通俗化,就多次用“全体意志”来代表“公意”:“既然只有全体意志才能约束一切属民,那我们就要研究这种意志是怎样表达出来的”,“由主权者制定的法令,只能够是全体意志的法令,即法律”。(28)
所以,问题其实在于,卢梭的“公意”究竟应该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伦理标准呢,还是应该理解为一种具体可操作的契约行为即立法行动?黑格尔认为是后者,他认为普遍意志作为一种抽象空洞的理念在实现为具体的立法行动时立即就会变质,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这样的结果是卢梭自己始料未及的。但其实卢梭要比法国革命那些理论家看得深远得多,也决没有黑格尔所以为的那样幼稚。他实际上早已看出,公意本身作为一条法律原则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原原本本地实现出来的,而只能当作立法过程中一个必须参照的标准来不断地接近。所谓“全体意志”所制定的法律不过是一种象征的说法,意指经过对公意的参考而制定的法律,而非指公意本身被制定成了法律。(29)就这种意义而言,李平沤先生下面这句话虽然找不到文本根据,但却是符合卢梭的精神的:“一个共和国应当把法律的制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应当把‘尊重法律’定为一切法律之中的第一条法律。”(30)这“第一条法律”不一定具有法律条文的形式,比如说它可以放在一部宪法的“序言”中以增加法律的权威性,(31)但它彰显的正是公意,因为只要真正在制定法律,没有任何一个参与制定法律的人会否定要“尊重法律”的。当然具体如何才叫做“尊重法律”,这还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和规范,在这上面就有可能产生不同意见并且需要投票表决,而这就属于众意了。
类似的公意还可以列举出一些来。例如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里“你的观点”不管得到多少人赞同,都属于众意,而你的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则属于一切人的公意,它正是卢梭所说的那种排除了各种相冲突的意见之后剩余下来的共同的部分,即言论自由。这是每个人不论观点多么冲突,只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想一想都会同意的。因为当你否定这条原则时,你不但否定了别人的发言权,你自己的发言权也就被否定了。上面黑格尔所说的“自在自为地合乎理性的普遍意志”,也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中或结合成国家而生活,其实也属于这种公意,但在卢梭看来这只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即国家是为每个公民谋福利的,而黑格尔却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是人世的神,人是为国家而活的。所以卢梭的公意可以成为一种契约,它基于私人权利的考虑;而黑格尔的普遍意志却只能是人必须无条件认可和服从的神圣信念。
尽管如此,卢梭的作为社会契约的公意其实和黑格尔的普遍意志一样,也是一种伦理原则和哲学理念,而不能直接等同于一种可操作的技术规范,所以对于建立国家的根据来说并没有什么层次不够的问题。卢梭在有些地方的表述甚至和黑格尔的普遍意志的理念非常相似,在他的最高层次的表达中也把公意和神相关联。如他说:“一切正义都来自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义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当真能在这种高度上接受正义的话,我们就既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法律了。”(32)现实的人类社会显然达不到上帝的这种正义,于是退而求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但是要这种正义能为我们所公认,它就必须是相互的”(33),也就是必须以一种相互缔结契约的方式而得到理性的确定,这就是公意了。但这种公意是以上帝正义为自己的楷模和理想的,所以就理想状态而言,最能体现它的社会制度或国家形式的就是民主制。但就具体操作的可能性而言,“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34)。他甚至还补充说,一旦勉强实现出来,则“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地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35)。这分明是预言和警告了法国大革命的那场灾难,因为凡是想将公意直接在众意中实现出来的,都必将导致众意对公意的摧毁。法国大革命正是由于忘掉了卢梭的这一告诫,才导致了失败(36),而直到今天,人们却还在像黑格尔一样指责卢梭的理论要为这一失败负责(37)。其实卢梭充分估计到了人性的有限性和恶,他的结论是:“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38)他之所以要鼓吹这样一种完全公意之下的民主制,不过是要为现实的国家树立一个理想的标准,以便随时检验现有政府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而已。
三、卢梭公意的根源:理性、情感和宗教
卢梭的上述公意既然不可能在现实的国家中完全实现出来,而只能作为现实国家完善化自身的理想标准而起作用,那么,这种公意就现实的人类而言又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上面已经有所提示。首先,公意是来自于人类的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卢梭也不例外。在卢梭看来,理性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出来进入道德状态的第一步。
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39)
对于当时盛行的自然权利学说,卢梭从中区分出来两种自然权利:一种是“建立在真正的但是泛泛的感情基础上的并往往会遭到我们的自爱心的制约的自然权利”,也就是“严格意义的自然权利”,它由“两个在理性之前起作用的因素”即自爱心和怜悯心构成;另一种是“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它不等于政治权利,而是更高层次的人权。(40)后者中起作用的就是超越于感情之上的理性,正是对理性的强调,才使得卢梭处处关注于意志的普遍性,主张法律是“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41),并致力于摆脱原始自然状态那种“毫无规律可言的自由”而进向一个普遍的社会(42)。就连最遭人们非议的那个命题,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43),也是基于人的理性之上的。当代伊塞亚·柏林等一些经验主义者觉得这一命题荒谬至极,觉得被迫的自由不可能是自由,正说明了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之孱弱。其实卢梭的推理非常简单,例如对罪犯处以死刑,他的解释是:“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话,自己也得死。”(44)后来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把这一原理表达为“罪犯受罚是他的权利”,黑格尔也基本上认可了这一说法。(45)
当然卢梭也看到,单凭理性还不足以使人类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自然法则(倒不如应该称之为理性法则)的概念是唯有当激情的事先发展使得它那全部的教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开始发展起来的”(46)。他并不认为自私而孤立的个人只要有了理性,于是“理性根据我们自身利益的观点就会引导着我们汇合成为公共的福利”(47),相反,人的自私会使人宁可违背自然法则的普遍规律而损人利己。以往人们只是凭借一个高居于人类之上的上帝权威的吓阻来避免这种自相残杀,但宗教带来的罪行并不亚于它所免除的罪行。即使近代以来哲学家提出了公意,但撇开个人的自私的利益,“假如公意就是每个人的纯理智行为”,又“哪里会有能够这样使自己摆脱自己的人呢?”人与人之间仍然是利害关系,每个人必须证明的是,“他的个人利益为什么就要求他必须使自己服从于公意”,(48)这甚至是不能诉之于传统习惯来解释的。然而,卢梭面对这样尴尬的困境并没有对理性失去信心。他说:“让我们努力哪怕是从坏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够医治人类的补救办法吧”,对于抱有怀疑的人,“让我们以新的知识来开导他的理性,以新的情操来炙暖他的心灵吧”,他相信:
有了强劲的灵魂和正直感,那个人类之敌就终于会放弃他的仇恨及其错误的,引他误入歧途的那个理性是会重新把他带回到人道上来的;他就能学会喜爱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到的利益更有甚于自己的表面利益的;……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49)
由此可见,卢梭的公意不是建立在一般的鼠目寸光的实用理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更高层次的、符合每个人的真正利益而不是表面利益的理性之上的。他不否认人性本恶,但他的整个“社会契约论”的设计,正是要从“坏事”、从恶里面锻造出整个社会的善来,让自私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理性意识到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这正是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它并不需要上帝的恐吓和愚民政策,而只需要对民智加以开发。
但另一方面,卢梭也深知民智开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人类虽然是理性的动物,但他们首先是欲望的动物和感情的动物,在自然状态中,他们的理性的使用只以满足自己个人利益的需要为限。我们不可能等到教会人们合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以后,再来建立一个完全合理的制度;而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人们又怎么可能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从而把自己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提升到合理的利己主义之上来呢?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如他所说:
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困难。智者们若想用自己的语言而不用俗人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那就不会为他们所理解。可是,有千百种观念是不可能翻译成通俗语言的。太概括的观念与太遥远的目标,都同样地是超乎人们的能力之外的;每一个人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是与他自己的利益有关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从良好的法律要求他们所作的不断牺牲之中得到怎样的好处。(50)
如何走出这一悖论?卢梭想到的是引入宗教来解开这一死结。他接着说:
为了使一个新生的民族能够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便必须倒果为因,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并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之前,便可以成为本来应该是由于法律才能形成的那种样子。这样,立法者便既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了。
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51)
卢梭指出,自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民族的父老和统治者们都要求助于神明,来使人民遵纪守法。因而,“在各个国家初创时,宗教是用来作为政治的工具的”(52)。卢梭并不像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那样,限于简单地批判和否定宗教,而是试图找出这里面的道理来。他通过历史的考察,把历来所有的宗教区分为三种:“人类的宗教”即基督教,“公民的宗教”即每个国家或城邦自己特有的多神教,还有“牧师的宗教”即独立于国家之外自成系统的宗教。他认为这三种宗教各有坏处:第三种最糟糕,几乎一无是处;第二种是政教合一的,还可以给国家法律带来一定的权威,缺点是欺骗和迷信;第一种是基督教,但卢梭并不看好今天的基督教,而是推崇从前“福音书的基督教”,也就是原始基督教,认为那和今天的基督教是全然不同的,它“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内心的崇拜,以及对道德的永恒的义务”,所以它是适合于全人类的(53)。“由于这种神圣的、崇高的、真正的宗教,作为同一个上帝的儿女的人类也就认识到大家都是弟兄,而且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社会是致死也不会解体的。”(54)但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形成了一个教士共同体,有自己的宗教法律,这“归根结底乃是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坚强体制的”(55)。为此卢梭对现行的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它作为“纯粹精神的宗教”宣扬对地上的暴君的奴性与服从,“它的精神是太有利于暴君制了”,“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出来就是做奴隶的”(56)。不过,尽管如此,卢梭仍然认为,宗教对公民社会是不可少的。他说:
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有很重要的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
因此,就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这些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则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57)
可见,卢梭对宗教的评价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公民社会,特别是有利于公民的道德责任,或者说社会公德,而这要由公民的社会性的感情即道德情感来判断。他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批判看起来是如此愤激,甚至因此被人视为无神论者,但仔细看来,这些批判主要是针对其有损于公民社会的外在方面,而对于宗教的内在方面,他毋宁说视为国家的基础。他认为原始基督教最接近公民宗教,但一切宗教中多少都含有公民宗教的因素,所以他主张宗教宽容,公民宗教应该是“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58)。他反驳那些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论调说:“对于这类言论能有什么坚强的答复呢?——假如我们不想用宗教来帮助道德,并使上帝的意旨直接参预人类社会的联系的话。”(59)在这一点上,他对待上帝的态度有点类似于康德。就像海涅说的,康德的批判是“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他已经袭击了天国,杀死了上帝,但是可怜的老兰培必须有一个上帝,否则就不能幸福,于是善良的康德出于同情又把天堂和上帝恢复了。卢梭也是如此,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充满丰富感情的浪漫主义者。他在凭理性推理时发现,他理想的民主制度单靠主权者的意志只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可是,为了使政府共同体能具有一种真正生存,能具有一种与国家共同体截然有别的真正生命,为了使它的全部成员都能共同协作并能适应于创建政府的目的;它就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我’,有一种为它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感情,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要求自我保存的固有意志”(60)。这正是受到黑格尔称赞的卢梭国家哲学的“内在方面”,按照卢梭的表述,它属于“法律的分类”中除了国家法、民法和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这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
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61)
而这种风尚和习俗历来是由宗教所维系的。卢梭在《日内瓦手稿》中说:“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62)而这也是一个民族的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公意”的基础。单纯合理的利己主义把公意变成了一种纯粹学术问题,如何才能更合理地实现每个人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不是一般群众能够轻易搞清楚的。直到今天,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就聘请专业律师。为什么相信律师?是因为他相信有一个绝对正义的公意,虽然自己不懂法律条文,但相信律师能懂,能够为他讨还应有的公道。所以,除了立足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理性之外,公意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就是宗教,它是基于全体成员共有的感情并形成传统习惯和风尚的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换言之,公意的根源除了理性,还有信仰,只有在这双方的共同作用下,才会有一种出自每个公民内心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效的普遍意志。
四、结论
黑格尔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公意理论的批评所包含的误解,与他自己对近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趋势跟不上趟有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63)。这一套“非批判的神秘主义的做法”“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64)。因此在国家理论方面,就对国家的神化而言,黑格尔不但落后于卢梭,甚至也落后于康德。(65)正因为他比卢梭和康德都更具有现实感,而德国的现实又落后于法国,这就促使他从理论的激进性上退后一步来适应现实。但卢梭即使在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氛围下也过于超前了,革命的领袖们忘记了卢梭的教导,急于一步就实现卢梭当作理想标准所设定的纯粹由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民主制,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恶。斯达尔夫人在革命结束后所写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这样回顾道:“经过十年动乱后,从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头脑中的热情已经消失,大家都开始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从果月18日以后,法国的革命已变成了一场走马灯似的换人游戏,上台的人只知道个人的利益而忘记自己的义务。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当成为后世人们吸取的教训。”(66)应当说是肺腑之言。
我们从卢梭的学说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呢?
首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所设计的国家政治形式包含有不同层次的原则,从最高的哲学理念到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当政治家们漠视这种张力而急于求成,则势必造成社会的大劫难。这一历史教训不仅适合于法国大革命,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政治革命,在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理想越是纯粹和纯洁,就越是容易被野心家利用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实行起来就越是残酷和血腥。革命中一切形形色色的“极左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过于“右派”或“中间派”,从实质上看无不根源于此。
其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多次强调社会政治体制与一国的地理条件(土地、气候、人口等等)密切相关,人们都批评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细看他的论述,不如说他是“文化决定论”,地理环境不过是他用来解释一国的文化传统所找来的理由,即所谓“风土人情”。那么,卢梭在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社会契约方案时重视一国的文化传统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既然社会契约是由人民缔结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人民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连续三章《论人民》来讨论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的是“从来不能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有的是早已过了青春期、不堪改造的老大民族,有的是国土庞大、人口众多却仍然以拼命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的不幸的民族,还有的是资源和人口不成比例的民族。根据他的分析,“俄罗斯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开化的”,他们注定要被鞑靼人所征服;(67)罗马人则不能不四处征伐,否则不能生存;最理想的缔造共和国的材料是科西嘉岛,他曾为他们起草过一部宪法。这些分析有许多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但说国家体制不能简单地横向移植则是不错的,要考虑每个国家的国情,充分意识到国情尚不适合的国家走上社会民主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第三,卢梭特别强调要建立人民主权的国家,首先必须有合格的人民,即能够作为主权者而形成公共人格或公意的公民。在这方面,两个必要的素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理性的推理能力,一个是可以充当“公民宗教”的信仰以及建立于其上的道德情感。这相当于我们常讲的“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如鲁迅的方案:“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然而卢梭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合格的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立”得起来;而民主社会又只有由合格的人民才能缔造。卢梭走出这一理论困境是求助于“神道设教”,通过宗教宽容而将基督教本身提升为“公民宗教”。那么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又该怎么办呢?
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向历史交上了一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的答卷;而80年代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则可以概括为“启蒙与改革的双重变奏”。不同的是,前一个双重变奏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道扬镳甚至对立,而后一个双重变奏则呈现出相辅相成的态势:启蒙的深化促进着改革的深化,而改革的进程也有利于启蒙的进程。人民在改革中所获得的最主要的收获,其实并不仅在于当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在于眼界的开放和思想的变革。对于知识界来说,目前的现实任务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进一步的启蒙,以便为下一轮更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总而言之,卢梭的“公意”理论直到今天还对我们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它奠定了现代国家理念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告诫我们不要教条主义地用抽象的原理直接套用于复杂的现实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思想的先行、启蒙的酝酿以及造就新一代公民人格要比推进具体的改革措施更重要,而在公意的形成方面,除了提高人民的理性思维能力以外,还必须寻求新的道德资源、建立符合人类感情的公民信仰。而在这些启蒙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之前,改革的行动只能被看作一种启蒙的手段,而不能指望一步到位,否则就很可能陷入黑格尔所批评而卢梭也早已预见到的社会灾难,(68)甚至导致历史的倒退。
注释:
①参看[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2页,译文据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157.有改动。
②注意这里特意将“共同意志”和“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就财产关系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而是另有所指的。所指为何?在下面的“附释”里就点出来了。
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82页,德文本第157-158页,译文有改动。注意,“政治权利”(Staatsrechte)和“政治义务”(Staatspflichten)均为复数,如果是单数,则译为“国家法权”和“国家义务”。
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82页,德文本第157-158页。
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83页,德文本第159页,译文有改动。
⑥⑦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5页;第146页。
⑧[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78页。
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4-255页,译文据德文本第400页,有改动。
⑩[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5页。
(11)高兆明认同了黑格尔对卢梭的这一批评,认为卢梭的公意“仍然取众意一致的形式,离开了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前提,就无所谓公意与众意之区分。而政治正义本身却是一个关于‘国家的哲学上的认识问题’,因而,它就是一个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的问题”。见所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第516页。但他未能看出这一批评并不符合卢梭的思想。
(1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8-259页,译文据德文本第403页,有改动。
(1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9页。黑格尔在这里打比方说,再坏的国家“就如同一个罪犯、病人或残疾者也是一个‘活人’一样”,类似于中国人讲的“子不嫌母丑”或“妈妈打错了孩子”。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18页。
(15)例如,李平沤先生在《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解释卢梭的话,即人民在选举一个国王的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个使自己成为人民的行为。“卢梭说,这后一行为就是人民的一个‘事先的约定’,即‘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抉择’。”“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它意味着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在这里,前一句话中的“即”字有歧义。它可以指“事先约定”本身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也可以指它的约定内容可以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也可能不是),而它本身则需要全体一致、无一例外地同意。后一句中的“意味着”也有歧义(卢梭用的是“假定”)。它可以指多数表决的规则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规则即全体同意,前一规则所显示的是后一规则的结果;也可以指前者本身就具有全体一致同意的意思,因此凡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场合就已经“意味着”全体一致了,所以就可以放心地让众意取代公意——而这正是法国革命对卢梭的理解。当然李先生这里只属于表述不严格的问题。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0页,着重号原有。
(1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1页。
(18)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人格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中意识到它自己的号数上的同一性的东西”(《纯粹理性批判》A361)。这也可以解释,卢梭为什么主张政府必须通过“定期集会”的改选而随时纠正偏差,使政府的运行始终保持在符合公意这个“公共人格”的轨道上(参看[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9页)。
(19)参看[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4页,译者注1;又参看第78-79页。
(20)参看《新世纪法汉大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générale”条。第二义项类似于后现代哲学家对普遍性的蔑视,带贬义,卢梭从来不用在“公意”上。
(2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5-116页,译文根据《黑格尔全集》考证版第9卷(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9,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0),第317页,有改动。
(22)德文gemeinschaftlich意思为“公共的”、“共有的”、“共同的”等。
(2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第122页,译文根据德文《黑格尔全集》考证版第9卷,第322页,有改动。
(24)(25)(2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5页;第33页;第33页注①。
(26)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第122页。
(28)(29)转引自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附录一,第170-171页;第115页。
(30)卢梭很清楚,一条法律以全票通过是极为罕见的。参看《社会契约论》第35页译者注④:“公意也就是众意,这是极其罕见的事。”因此,如果要把国家建立在这种特例上,那国家就永远建立不起来了。
(31)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和第五共和国的宪法都将“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部分纳入,其中包含的各条均为公意性质的条款。
(32)(33)(35)(3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45页;第45页;第85页;第87页。
(3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4页;又见第140页:“真正的民主制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36)李平沤先生说得好:“卢梭是把法律放在哲学的范畴来思考的,而罗伯斯庇尔则把法律作为一种开辟新的政治途径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参看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第118页。
(37)人们对卢梭的另一个指责是他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其实并不确切。在技术性操作层面上,卢梭并不反对三权分立,反而主张分权制,因为否则只能形成一种“没有政府的政府”(《社会契约论》,第84页,又参看第51页,谈到“号令人的人”和“号令法律的人”不应该是同一人。也可参看最新出版的《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2006),马克·戈尔迪、罗位特·沃尔克主编,刘北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54页:卢梭“与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国家必须实行分权”。该章出自德国学者Iring Fetscher)。他反对分权制只是因为不能把这种“法律的应用”(“主权所派生的东西”)的技术规则转移到“法律”本身(“主权权威”)上来(《社会契约论》,第34页)。可见把后来的极权主义归咎于卢梭是毫无根据的。黑格尔也反对三权分立,但他甚至在技术层面上也主张三权和谐合作,所以在这方面他比卢梭还不如。
(39)(41)(43)(44)(46)(47)(48)(4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5页;第47页;第24-25页;第42-43页;第188页;第189页;第191页;第194页。
(40)参看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第127-128页。
(4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附录《论普遍的人类社会》,第187页。这是《日内瓦手稿》在发表时被抽掉的一章。
(50)(51)(52)(53)(54)(55)(56)(5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3页;第53-54页;第55页;第173页;第175页;第173页;第179页;第180-181页。
(58)(59)(60)(61)(6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83页;第190页;第76-77页;第70页;第166页译者注③。
(63)(64)[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4页;第348页。
(65)参看[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载于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23页:“一个国家(civitas)就是一群人在法权法则之下的联合。”其中第47节几乎就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逐字复述。
(66)转引自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第112页。
(6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8-59页。
(68)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中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视为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绝对精神由此而从“教化”过渡到了“道德”和“良心”,人的素质及对自由的把握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应该可以不让历史的厄运重演,而可以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